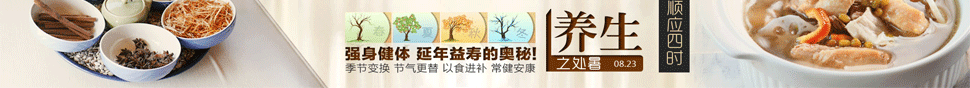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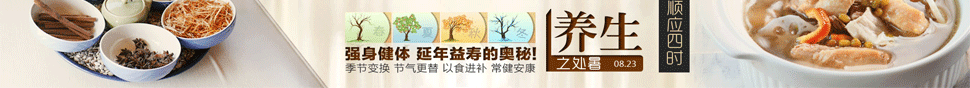
青春、热情、理想主义;风华正茂、挥斥方遒、锦瑟年华。
对青年的联想总是热烈的,正如歌德所说,“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,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。”
不管在哪个年代,青年,都被视为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本期书单介绍的书籍,它们或是影响不同时代青年群体的精神符号,或是献给广大青年的箴言。跟随它们,一同踏上青年的意气风发之旅。
“觉醒年代”的青年理想
“无精神生活的人,知识愈多,痛苦愈甚”
上世纪初,一本杂志横空出世,名为《新青年》。该杂志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,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,在“五·四运动“期间起到重要作用。
《新青年: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》这本书重现了著名杂志《新青年》掀起的思想波澜,那个时代的青年精神与风骨从书中可见一斑。
彼时的“新青年”是如何立危墙之下仍不忘家国担当,又是如何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实现人生理想?陈独秀、胡适、蔡元培、钱玄同、鲁迅、周作人、瞿秋白……所有这一切通过这本书与如今的青年们展开了一场无声的对话,无论时代怎么巨变,青年的一腔热血从来都是年轻岁月最好的勋章。
在《新青年》杂志发光发热的20年代,梁启超先生也倾注热情举行了三十场讲演,关乎教育的出路,关乎青年的自救行动。而这三十场振聋发聩的讲演在当时深深影响了一批“新新青年”,包括周恩来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吴其昌、刘节等等。
《致“新新青年”的三十场讲演》便是对梁启超讲演稿的全面汇总,时间跨度为年至年,可以视作“前浪”对“后浪”最诚挚的寄语。
在梁启超看来,做学问也好,读书也罢,最主要的事情不是求知,而是有丰富的精神生活。于是他说:“无精神生活的人,知识愈多,痛苦愈甚。”更是提出“精神饥荒”这一说法,并发自肺腑地给到广大青年们自救的建议。
书中,梁启超还重新定义了新文化,即在科学和民主之外还要加上道德自律。同时他十分重视创造与劳作的乐趣,反对毫无趣味的倦怠劳作.....很多主张放在百年后来看,仍鞭辟入里,对当今的青年仍有指引意义。
年1月,周树人参加《新青年》改组,任编委。同年5月,他以“鲁迅”为笔名,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载在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。
鲁迅对青年群体一直非常关心,在他的作品与书信集里,常能看到他对青年群体的关切和期望。柔石、白薇、萧红、萧军等文艺名家,都曾在青年时期身受鲁迅的提携、指点。
在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一》里,鲁迅这般寄语青年: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,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,就令萤火一般,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,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竟没有炬火:我便是唯一的光。”
同样心系广大青年的还有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,他在20年代末期旅欧期间,从海外寄回了十二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,整理成册便有了这本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。
书的内容涵盖颇广,涉及到读书、升学、作文、做人、修身、谈情、爱恋等方方面面的话题。有现代读者阅读后感叹:“这十二封信啊,愿对于现在的青年,有些力量!”
朱光潜俨然一位亲切的前辈,字里行间没有说教的口吻,更多的是有理有据的劝慰,譬如他提出的这条建议,就颇为暖心:
“朋友,闲愁最苦!愁来愁去,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,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。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,你对于烦恼,当有‘不屑’的看待;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,你对于烦恼当有‘不值得’的看待。我劝你多打网球,多弹钢琴,多栽花木,多搬砖弄瓦。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,你就谈谈笑笑,跑跑跳跳,也是好的。”
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朱光潜告诉我们“眼光要深沉,要从根本上做功夫,要顾到自己,勿随了世俗图近利”,即便在今天,这番建议仍是字字珠玑,段段入心。
文学、在路上、摇滚
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”
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我们迎来了肆意洒脱的阅读松绑,经典的西方文学以延迟的状态开始被大量中国青年阅读,甚至有一种说法是:男生必看《红与黑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女生必看《简爱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它们打开了一代人的视野,帮助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理想、追求与趣味。
年,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开始翻译进入国内,年出版的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》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先锋派青年作家,启迪了余华、格非等作家。再后来,马尔克斯、卡尔维诺、波拉尼奥等文学大师的作品纷纷进入国内,持续震荡着中国文学青年的心灵。
约翰·列侬、摇滚与理想主义则为当时的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冲击,他们影响了国内第一批摇滚乐队和音乐人。许巍说:“我当初走上音乐之路就是因为对‘披头士’乐队的喜爱,英国摇滚文化对我的创作影响是最大的。”崔健曾评价,“披头士的意义,就是将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,这才是摇滚乐。”
尼采和萨特带来了哲学的流行,《悲剧的诞生》和《存在与虚无》成为80年代大学校园的热门图书。年,李泽厚创作的《美的历程》出版,掀起了“美学热”的潮流。年,黄仁宇创作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出版,影响了一众作家和高校研究生。
年,《在路上》的译者陶跃庆首次接触到该书的英文版,这本书被称为“垮掉的一代”的经典之作,开始影响部分中国青年人,他们被那句“我还年轻,我渴望上路”深深打动,纷纷踏上漫游之路。
当然,还有金庸古龙的武侠作品、琼瑶的言情小说,是当时的青年人最爱租赁的图书。
我们迎来了中国文学浪潮的一次喷发,年,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出版,年,余华的《活着》、贾平凹的《废都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同年出版,年,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出版。作家路遥出版于八十年代后期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至今仍排在大学借阅榜前列。
三毛作品的流行也有着特别的意义,她放任恣肆的语言风格、漂泊自在的生活方式,某种程度上启发了一代青年的自我意识。
还有以海子为首的当代诗人们,为我们贡献了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最浪漫的想象,至今仍萦绕我们心中。有多少人曾默默在心底对自己说,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”。又有多少人在应景时分感怀那句,“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”.......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,也是无数青年想到抵达的精神世界。
新的世界,新的挑战
致正在追求和创造新的生活的青年们
我们正在面对的世界,复杂程度远超过往,为此,我们需要新的智慧与指引。
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,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极具影响力、极受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baiweia.com/bwcd/15860.html

